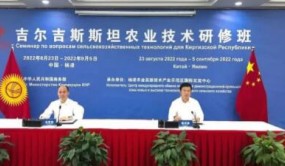出生和死亡的节律设定了人口扩大和收缩的进度。年景好,人们就会养育更多的孩子或者说,更多的孩子能活下来。久而久之,新一代膨胀的需求推高了粮食价格,反过来还鼓励一些农民去寻找和耕作一些边缘的地块。
更大的需求导致了更高的价格,这使人们去开发相对贫瘠的土地来讨生活,但是要养活越来越庞大的人口,用这个策略注定会失败。最终,产量会下降,放大的人口也更容易遭遇饥荒。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都会非常有规律地进入这个人口数量增长和下降的周期。疾病时常伴随着饥饿让人虚弱的影响,也成了杀人利器。而且还有战争的创伤,军队洗劫农村,会使那里的生活处境更加糟糕。
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致使德国人口下降了35%,给16世纪的人口增长画上了一个突然的句号。一些简单的经济真理主宰了一切。食品丰富,价格下降;食品短缺,价格上涨。人口增长增加了需求,从而推高了粮食价格。随着人口数量的减少,粮食价格会下跌,农作物种植面积也会缩小。现代化以前,农民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也养不66活足够的牲畜,不能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所以他们一直心存对坏年景的恐惧。
这挫伤了投资的信心,增加了对权威的依赖。最好为拮据的日子提前储蓄;最好不要冒犯那些在困苦时期能提供帮助的人。因为收成不定,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在这些情况下,宿命论盛行。只有农业生产力提高了,恶劣天气才会显得不那么生死攸关,人们才会愿意相信自己有掌控命运的能力。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口在增长和下降之间大起大落。14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大陆,人口数量几乎触底。
来自中国的大篷车里的老鼠身上的跳蚤把黑死病带到了欧洲,不到四年,欧洲的人口几乎死了一半。因为黑死病周而复始地爆发,所以15世纪,欧洲人口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亡率居高不下。人口的连续损失致使整体经济紧缩。消费者减少了,而且分散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货物的运输成本变得非常昂贵。许多贸易关系骤然中止。但是人口减少对幸存者往往意味着更美好的时代,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工资,从地主手中获取更好的租约,地主们被迫开始争夺租户。
工人数量的减少也激励了葡萄牙的贸易商,他们沿非洲西海岸扬帆航行去买奴隶,并把他们带回里斯本。人们为了应对早先的人口增长,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现在人口下降,人们放弃了这些定居点。15世纪中后期,英国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村庄不复存在。16世纪初,欧洲人口开始从黑死病中活过来,但是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的人口数量才达到公元1世纪的基准值。人口增长与收缩的秋千荡来荡去。
16世纪,人口增长,17世纪,人口又下降了,到18世纪40年代,人口又出现了新高点。 这一高点成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的永久出发点。自此以后,虽然19世纪早期,欧洲大陆仍经历了几次饥荒,但是人口缩减停止了。18世纪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时刻在思考这些现实问题,他发表了著名的《人口论》。 他在书中揭露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困境。
他从一个人口增长的简单假设开始: 如果食物充足,人们就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而这幸福的产出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饥馑。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口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如果一对父母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很快就会有36个孙子孙女,家庭人口等于增加了六倍。
即使农业扩大,更多的土地可以投入生产或增加产量,它也只能缓慢地以算术方式增长一一二加二,而不是二乘二。粮食种植增加10%,产量只能在每100蒲式耳的基础上多出10蒲式耳,几乎不够养活新增人口。饥馑加速袭卷重来,新耕地也不如已开垦的土地,因为人们首先会耕种好地,只有当需求推高了粮食价格,他们才会迁移去贫瘠的土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言外之意令人震惊:生育可以消灭所有大丰收带来的丰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