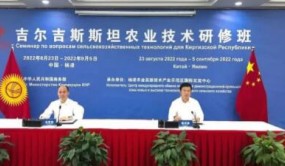经济史研读:物质资本对工业国和农业国的经济影响并不相同对整个国家而言,增加物质资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经使用的自然力量转变成为物质资本,转变成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工具;而就单一的农业国来说,有着许多闲置的、原封未动的天然力量,只有通过制造业才能使之活跃起来,变得有用。他同样没有考虑到,制造业对国内外贸易、对国家的文明和实力、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由此取得的物质财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影响。
他没有考虑到,英国通过殖民手段取得了多么庞大的资本(马丁估计数额在二十五亿英镑以上)。尽管在别的场合他曾那样清楚他阐明,中间商业环节的资本,只要还没有在某一国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就不能认为它是属于该国的。但他在这里却没有考虑到,这种资本,对本国制造业是非常有利的。
他同样没有考虑到,通过实施有利于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大量外国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被吸引到了本国。他错误地认为制造业会按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自发地形成并按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他没意识到,为了国家的特殊利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势力总要对这种所谓的自然进程加以干预,使之朝着人为设定的方向发展。
他用模棱两可的方法和因而根本错误的表达方式引用了一个根本错误的例子,他试图举例证明:因为用人工方法在苏格兰酿酒这种做法不明智,所以用人为方法建立制造业也是愚蠢之举。
他把一个国家的资本的形成过程,简化为一个收租者的私人行为,收租者的收入确实取决于其物质资本价值,但他只有通过储蓄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然后才能把收入转化为资本。
他没有看到,对商人来说这种储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整个国家都遵循这个理论,则必然导致贫困、狭隘、无能和国力衰败。既然人人竭尽所能热衷储蓄与节约,那么生产的动力就不复存在了;既然人人都只是考虑交换价值的积累,那么生产所需的精神动力就会减退。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这样一些如此愚昧的守财奴,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为了担心负担战争费用而放弃保家卫国;只有当他们的全部财产因为外敌入侵而被掠夺一空时,他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真谛:国家财富只能通过与收租者完全不同的方式才能获得。
作为一家之长,收租者个人应遵循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应与这里提出的店主式的物质交换价值理论完全不同。他必须至少支出足够多的交换价值用于教育后代,使他们待日后财产转交到他们手中时,能够承担起管理重任。
国家物质资本的积累,应采取不同于收租者单纯储蓄的方式;国家物质资本积累所采取的方式与生产能力的积累所采用的方式相同,主要是通过国家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农业、制造业和商业资本之间的交互作用。
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国家精神资本的增长;反之亦然。农业物质资本的形成有赖于制造业物质资本的形成;反之亦然。
商业物质资本处处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在制造业资本与农业资本两者之间起着协调与补充作用。
在欠文明国家,在渔夫和猎户为主的国家,自然力量几乎无所不能,而资本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国外贸易虽然会使资本有所增加,但是这样做(通过枪炮、火药和铅弹)会使自然力量的生产能力遭到彻底破坏。储蓄理论对一个猎人毫无益处,否则他必将没落或者改行做一个牧羊人。
在畜牧业为主的国家,物质资本会很快地增长,但是只有当自然力量能够同时为家畜提供充足的饲料时,这种增长才会实现。家畜以及生活资料增长以后,人口也会随之增长。一方面,大量牛群和大量羊群以及大牧场被分割成了许多小群或小块,另一方面,国外贸易诱导消费。向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宣讲什么储蓄理论将是劳而无功的,国家必须从畜牧业国转变为农业国,否则也难逃贫困的命运。
就农业国家来说,它利用闲置的自然力量增加财富的空间虽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
农民自己可以储存粮食、改进土质、增加畜群数量,但是人口总是随着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长的。生活资料越丰富,人口也越增加,物质资本(即耕地和家畜)就会被增长的人口分割得更为零碎。但是光靠辛勤劳作是不会使土地面积扩大的,而且由于运输工具的缺乏——如前一章所述,这是因贸易不发达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欠缺结果——对于土地的潜在力量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另外,单一的农业国家最缺乏的是通过制造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所赋予国家的那些手段、智力、活力、进取心以及社会发展,因此单一的农业国家的农业人口不久就会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即农业物质资本不再与人口的增加保持同步,国家的资本总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国民的贫困却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最主要的物产就是人,他们既然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够丰衣足食,那么就要向国外迁徙。流行学派把人看成是一种积累资本,但对人口迁移的国家来说,这种说法却很难令它感到欣慰;因为人口的输出不但不会引致带回货物,反而会适得其反地造成大量物质价值(如工具、家具、货币等)的非生产性输出。
处于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国内分工还没有完全发展,因此无论是勤恳还是节约都不能增加物质资本(即个人的物质富裕)。
当然,作为一个农业国而绝对没有任何国外贸易的情形是很少的;国外贸易,就它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关于资本增长这一点,也会带来国内制造业的发生与发展,因为它由此使外国制造商与本国农民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毕竟只是局部的,而且缺陷极大:首先,这种商业活动只限于某些大宗产品,活动地区主要是在那些沿海口岸及通航河流一带;其次,这种商业关系总是极不规则的,遇到战争、商情变化、贸易法规的改变,或者遇到国外获得大丰收或输入方面的变化,这种关系常常会中断。
因此,要使农业物质资本有规律地并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增长,只有在农业国建立起完全发展的制造业才能得以实现。
迄今为止,一国的物质资本绝大部分总是与土地密切相关,不论哪一个国家,地产、城乡住宅、厂房、工厂、供水设备、矿山等的价值大约要占国家全部资产价值的三分之二到十分之九。因此,凡是使不动产价值有所增减的,也会使国家物质资本总量有所增减,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个通则。很明显,具有同样肥力的土地,它的资本价值,邻近小城市的,比在偏僻地区的不知要高出多少倍,邻近大城市的,比邻近小城市的又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至于制造业国家与单一的农业国家,双方土地价值相差悬殊,简直无法比拟。反之,也可看到,城市住宅与制造业建筑物连同它们的地基的价值,总是随着城乡商业关系的扩大或收缩或者是随着农业的兴衰作等比例地升降的。由此可得结论:农业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制造业资本的增长;反过来,后者的增长也依赖于前者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