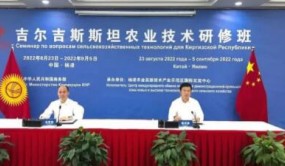所有的经济首先都是粮食生产。我们知道这一点,但这一点并不直观。处处林立的商场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使我们感觉不出稀缺可能的模样。饥荒只发生在其他遥远的国度,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然而,饥荒曾经像恶劣天气一样常见。
虽然中世纪构造了美观的建筑,还成立了大学,资助了战争,但是欧洲国家-连同世界其他地区-常常没有足够的粮食。富人在收割第一茬庄稼前的几个月里,可能还有充足的食物,但大多数人则不得不勒紧腰带,希望他们去年秋天贮藏的胡萝卜和芜菁还没有发霉,希望晚霜不会耽搁春季的播种。那些年月,保存食物的方法很少。没什么收成的日子里,农民只能吃为春季繁殖而越冬饲养的动物,或是吃为第二年播种储备的种子,否则他们的处境会非常艰难。
饿死的情形虽然不常见,但歉收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现在分析,我们认为用更少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粮食非常必要,如果国家想支持其他经济追求,只有农业重组才能释放工业等其他经济活动所需的工人和资金。稀缺在现代化以前的社会具有普遍的影响。政府当局会仔细观察每年收成的变化,为来年储备粮食。官员们总是监视着农民的一举一动,害怕他们会把粮食撤出市场,等粮食价格上涨时再出售,或是未经许可就把部分粮食卖给酿酒商。
对饥荒的恐惧促成了普遍的监督。粮食的种植和销售落在了一大堆法规条例的漩涡里。每个国家的法律都反映了政府当局对饥荒及其引起暴乱的担忧。小麦、大麦、燕麦和大米-这些组成主食的珍贵谷物-的每一个生产步骤都受到监视。行销三大罪-独占、囤积和倒卖-在英国法律里都是重罪。这些十恶不赦的行为是什么?购买大量的食品,把它们撤出市场,等价格上涨后,再卖给他人。这些名字非常古老的旧法规肯定了粮食种植与销售和经济活动一样是社会行为。
人们不认为谷物是可以穿过农村,寻找最优价格的商品。种植谷物(英国人称为玉米)的农民-佃户、自耕农或地主-并不真正拥有谷物;他只是把谷物从田地运到当地市场。他不能储存谷物,也不能把它送去远方的市场,而且作物在田里生长时,他也不能把它卖给中间人。他只能把家人吃不完的谷物装进马车,送进最近的市场,把这些粮食卖给老主顾。加工面粉的磨坊主和再加工的面包师同样也受到限制,他们必须有序地进行加工,直至最终制作出一个面包,然后以当地巡回法院设定的价格售卖。
即使到了今天,饥饿仍是数百万人不得不面对的悲惨现实。几年前,《纽约时报》报道了中非共和国发生的饥荒,它描述了一个农民让妻子把最后的一点小米熬成粥,这样他们才都能活下去。大多数人或许没想过,制作面包或酿造啤酒的谷物与为来年准备的小麦或大麦种子是一样的。人们因持续的匮乏,往往会无法抵御诱惑,吃掉他们为下一季预留的种子,中非共和国农民这样的做法将会在未来产生可怕的后果。
传统社会的人们谋求的是欣赏自然,而不是干扰自然,他们对社会安排充满了敬畏和虔诚,反之现代人经常思考的却是革新。接受与顺从的每日哲学不仅可以抚慰疼痛,而且鼓励人们尊重意志力,忍耐艰难的岁月。政府当局强加的稳定规避了许多不良后果,但也抑制了新思维。一成不变的忧心孕育了某种死气沉沉的氛围。
只有借着想象进入资本主义以前的旧秩序,我们才可以理解创新者为了改变它进行的斗争。道德经济从维持社会稳定到促进发展的转变并不是在一个世纪就实现了的。16世纪,当时的人还不能感受到商业世界的魅力。都铎王朝的法令规定了工资、济贫和收获谷物,它的法典精神依赖强大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基础包括上帝命令亚当一直工作到汗流浃背,以及阿摩司严酷惩治那些“吞噬穷人”的人。
圣经经济的显著特点与16世纪欧洲为了控制信仰的劳动秩序完全一致:世界因劳动而硕果累累;对人类来说,劳动既是罚,又是礼物。作为礼物,劳动实现了人类社会与上帝恩赐的结合。作为惩罚,劳动永久驾驭着人们完成维系生活和遵从神祇的共同工作。圣经解释了社会秩序,为日常任务赋予了神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