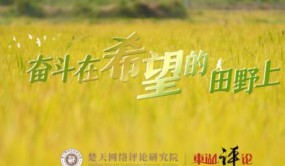摘要:“空壳社”与合作社异化均对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及时清理“空壳社”的同时,研究者需要深度辨析形成“空壳社”与“异化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本文通过机理分析和案例研究,借助Williamson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论证了合作社的异化与部分空壳社的形成是由于合作社交易成本问题而产生“理性选择”的结果。“空壳社”的清理不能搞“一刀切”,应该通过构建“社员-合作社”的“置信承诺”机制来有效控制合作社交易成本,并探索以合作社为媒介,促进合作社内部社会化服务供给有序,激活合作社发展潜力,这将成为防范合作社异化和“空壳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空壳社”;合作社异化;交易成本;置信承诺;社会化服务
一、引言
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后文简称《合作社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步入“快车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与参与人数与日俱增,在带动小农发展、完善社会化服务、助力脱贫攻坚与提升农业效率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如出现大量“空壳社”、“僵尸社”、异化的合作社。合作社发展的路径并没有遵循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需形成专业化、组织化、系统化、社会化发展的既定目标前进。甚至学界与业界纷纷质疑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合作社(邓衡山等,2016;邓衡山等,2014)。合作社发展的质性漂移、名不副实已经严重压缩了合作社未来的发展空间*。为有效规范合作社的运行,提升合作社的发展质量,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于2019年2月联合印发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后文简称《清理方案》),对一些不能正常运行的“空壳”合作社进行清理注销,这标志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正式迈出了从注重总量到追求内涵的重要一步。
在《清理方案》出台后,业界与学界普遍认可“空壳社”清理的必要性,同时也表达了对“空壳社”清理过程中政策工具的使用泛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忧虑,担心未来有资源、靠套取政策资金发展起来的虚假合作社依然存活,而那些坚守合作社质性规定,但市场运作能力弱的合作社却被清理出局,这种情况的出现将进一步弱化我国规范型合作社的存在度,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也违背了《清理方案》意在提升我国合作社发展质量的初衷。在贯彻落实《清理方案》的同时,有效避免清理空壳社造成的“误伤”和“错杀”,进而将合作社规范发展落到实处,必须完成对以下关键性问题的解答。(1)为什么会出现空壳社,空壳社是不是一定是合作社异化的产物?(2)是合作社异化造成的危害大,还是空壳社的危害大?(3)出现“空壳社”是不是一定要清理?清理“空壳社”就能实现合作社发展优化吗?(4)规范合作社发展的政策立足点在何处?应该坚持怎样的合作社质性原则?扶植什么样的合作社有助于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合理解答,将有助于本文辨析清楚“空壳社”与“异化社”之间演化的内在逻辑关联,对于增进合作社的“内涵”建设意义重大。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通过文献评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空壳社”形成、合作社异化的原因进行阐述,厘清空壳社与合作社异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其次通过机理研究说明合作社的异化才是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空壳社”的清理并不能完全解决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全部问题。同时本文亮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问题是市场导向的结果,异化社更应该纠偏,任其发展将对农业经营主体创新产生更大危害,有效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化解合作社异化问题最为关键。接着本文展现了四个不同类型合作社的发展轨迹,再次说明并不是“空壳社”就一定不规范,不在清理范围的所谓“示范社”其实对农户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证明“空壳社”与“异化社”需要分类对待。最后根据相应的研究结论,在合作社规范发展、提升合作社经营能力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合作社质性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前期(2008年前)。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引入西方合作经济理论,并用其来诠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实环境。其中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Hendrikse等,2005;Fulton等,2001;Cook,1995;Fulton,1995;郭红东等,2005;李金波等,2010),如研究合作社适度规模化经营对促进农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唐宗焜,2007;应瑞瑶,2006);成立合作社对改善农户市场弱势地位的必要性研究(石敏俊等,2004;黄祖辉等,2006);国家与合作社建设的关系论证研究(苑鹏,2001;黄祖辉,2000),以及合作社组织创新与异化的内涵界定研究(应瑞瑶,2002)。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多地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是一种创新形态,是符合时代特征和中国现状的改革财务(黄祖辉,2000)。
在合作社发展的井喷阶段(2008—2017年),合作社理论研究者既认可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取得的成就,也认识到合作社发展存在质性漂移的趋向(黄祖辉等,2009)。相关研究关注三个维度,首先是用经典合作社理论来诠释合作社存在质性漂移的原因(郭晓鸣等,2010;蔡荣等,2011;张晓山,2009;马彦丽等,2008)。其中熊万胜(2009)将中国合作社的演进归位为“制度化进程中的意外后果”;邵科等(2008)以社员入股额度作为参考变量,验证了成员异质性使合作社治理结构产生异化;崔宝玉等(2012)分析内部人控制造成合作社治理失范的原因。其次,研究者依然关注合作社在组织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层面的绩效研究(蔡荣等,2011;徐旭初等,2010;杨丹等,2015)。其中周振等(2015)以仁发合作社为例,论证了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的改进,能有效激励资本、土地、劳动要素的投入,从而促进合作社经营规模的扩张;崔宝玉等(2017)的研究发现经济绩效与社员收入绩效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最显著。相似的研究还包括张俊等(2015)从专家、管理者和社员三方视角分析合作社绩效的构成;彭莹莹等(2014)分析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等。最后研究关注实现合作社治理优化的演化途径(Benson,2014;Yang等,2014;许建明等,2015)。其中管珊等(2015)提出强化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建立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能促进合作社治理优化;崔宝玉等(2017)提出按交易额分配盈余能有效控制交易过程中商品契约的剩余风险,通过对积极社员和核心社员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组织与管理的合理补偿来理顺合作社内部关系治理,从而使关系型治理机制反向促进交易额分配盈余返还机制良性运转。
另外,有部分研究表达了对合作社异化的担忧,从组织嵌入、合作社质性规定深入探究了合作社形成异化的根源(张益丰等,2016;邓衡山等,2016;潘劲,2011)。最具代表性的是邓衡山等人的研究成果(邓衡山等,2014;邓衡山等,2016)。相关研究认为由于我国的农产品质量监管不完善、农户异质性强且经营规模弱小、同时缺乏有效的外部资源支持(尤其是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导致规范合作社的生存环境变差(产业链上游实现横向一体化的优势被弱化,高组织成本的劣势被放大)。政府的政策诱导、合作社的遴选机制不健全、对合作社日常运行的监管机制失位等原因是合作社走向异化的根源(邓衡山等,2014;潘劲,2011;仝志辉等,2009)。相反的观点来自徐旭初等(2017)的研究,认为具有合作制属性的合作组织或类合作组织,都可以算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
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从追求数量向内涵发展过渡,2017年后合作社研究更强调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提升实现机制,探索以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机理与可行性方案设计(张益丰,2018;崔宝玉等,2017)。研究认为只要存在要素契约与商品契约相互治理,并且商品契约对要素契约形成反向治理,真正符合合作社质性规定的合作社是可以存在的(刘西川等,2017)。张益丰(2019a)进一步提出社会关系治理是维系合作社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交互治理的有效联结机制。通过以合作社为平台,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将会促进社员与合作社的利益相融(张益丰,2019b)。随着“空壳社”治理的推进,相关学者就“异化社”、“空壳社”形成类型、主要原因、组织优化路径进一步进行了论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等,2019)。其中应瑞瑶(2002)对异化社的定义最宽泛,研究认为凡是“大股东控制普遍,普通社员收益不多”的合作社多为异化社。罗攀柱(2015)认为合作社异化是合作社偏离合作社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等(2019)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空壳社”就是无生产、不运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异化社的定义相对较窄,研究认为本身不是合作社,出于套取“政策优化条件”为目的,将自己包装成合作社的组织才是“异化社”。
王忠林(2019)对空壳社做出了较为精准的界定,研究认为所谓“空壳社”就是有名无实的合作社,既包括因为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空壳”,也包括由于自身机制错配造成的“空壳”,也就是“虚假”合作社。研究进一步指出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空壳社与虚假社野蛮生长的原因就在于当前我国农业合作社未坚持按照“主要按交易量(额)分配”的合作社基本原则运行而造成的。
在上述研究中,尽管这些理论文献对合作社发展路径、发展绩效评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有几个关键疑团依然未得到解答。首先当承认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先市场化后合作化的特殊发展轨迹,空壳社的存在和异化社的生成是否是合作社顺应市场发展过程中“理性选择”的产物?合作社的清理到底是“一清到底”还是应区别对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空壳化”与“异化”过程是否存在交集?在帮助合作社成长如何在防范合作社“空壳化”的同时,抑制“异化社”的形成?前人的文献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前合作社概念的泛化*,以及对合作社治理对象的外延,使得众多企业行为、契约交易行为均纳入到合作社治理范围,异质性的经营模式与收益分配形式导致合作社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直接影响到合作社治理成效。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将针对上述问题,试图利用机理分析和案例展示来解答它们。